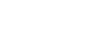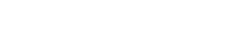上千叛徒軍人 告白「我如何製造仇恨」
門被焊死、窗戶裝上老鼠籠般,密密麻麻的鐵窗,整條街只剩死者的名字、嵌在牆上的照片,正中午的「鬼鎮」,只有寒慄。
中央市場、1800個店家,跟一旁的公墓相同,沒有人聲。
這裡是巴勒斯坦西南最大城,世界上最早有人居住的城市,也是猶太教、伊斯蘭教、基督教最重要的聖地之一:希伯崙(Hebron)。
1997年後,這裡是唯一在市中心內,移入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城市。六百個猶太人移入,圈起市中心的20%土地;水泥牆、檢查哨和七百個軍人,把18萬巴勒斯坦人擋在外 。
「滾開!」突然,謾罵聲朝我們追來。
一群蒙面小孩,拿水杯對我們潑,「你不羞恥嗎?你們這群叛徒!」
這群以色列小孩攻擊的「叛徒」」,也是以色列人,為我們帶路的邵爾(Yehuda Shaul)。
十年前,他是以色列特戰部隊的指揮官,就在希伯崙,奉命保護屯墾區居民。
全身濕的他繼續導覽,「這些門焊死的時候,裡面還有人住,所以他們要回家,只能從其他人的屋頂爬回來,」他講解服役時,士兵如何「創造」廢墟:例如,半夜闖入民宅,抽查人口,帶走小孩:例如,一條街上設三個檢查哨,或突然封街。
「如果是你,你還能在這裡過活嗎?」邵爾問。
在面積僅台灣六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地區,有兩百多座以色列屯墾區、六十四萬名屯墾居民,這類以色列小鎮,成為衝突的「前線」。
占領滲進生活,仇恨也種進三代以巴人民心中,互施、互控暴力,循環不停。
但屯墾區發生的事,2004年之前,多數以色列人一無所知。
「打破沉默」(Breaking the Silence,以下簡稱BTS)」在2004年建立。「你們把我們派去那裡,以你們之名,我們做了這些,現在我只要求你們聽一聽,」邵爾與同袍們將自己所作所為紀錄、上網,舉辦攝影展,掀起國內外討論。
至今,1100位軍人加入作證,每年,海內外超過400場演講邀約,德國外交部長到訪,也指名與BTS見面。
但是,BTS在其政府的口中,是叛徒、恐怖組織,今年六月,法務部長發動檢調,調查BTS發言人是否於服役時犯罪。
政府反應如此劇烈,因為這些軍人的日記,就是證據。
例如,以預防暴力為由,長官下令殺人;例如,為訓練新兵,指揮官要求菜鳥挑一戶巴勒斯坦平民,進行模擬逮捕,破門、毆打、逮捕、審問,然後放回。
例如,面對非暴力的遊行抗議,軍方指導手冊的步驟之一,是抓最小的小孩。
邵爾還說:「還有一份作證,是一次恐攻之後,上頭派了三個小組,指令是在隔天凌晨兩點,無差別的在檢查哨殺人、報仇,」15條人命因此喪生。
從上千份證詞中,他們發現以色列軍人的四項任務。
首先,製造恐懼。「讓巴勒斯坦人隨時覺得自己在被追捕,我們就在他的這裡(拍後腦勺)」,盡可能讓軍人存在感放大,且不可預測。
第二,預防。對炸彈客進行「預防式狙擊」,逮捕嫌犯的家人、拆毀家屋等。
第三,分隔。把農夫與農地分開,離間巴勒斯坦的社群,蓋圍牆或封路,把村落孤立。
第四,執法。按法律,以色列警察有權管束屯墾區居民,軍人有義務要保護屯墾區,於是當警察不在場,軍人常為夾心餅乾,供居民使喚。
這些,媒體不報導、人民不知情。軍人腦裡的記憶,就像屯墾居民潑的水,蒸發了。
即使民眾知道了,也會認定,對方是暴民,制裁理所當然。
八月初,以色列法院宣判一名士兵十八個月刑期,因為他在執勤時,對著已無行為能力、攤躺在地的巴勒斯坦嫌犯,行刑式直接斃命。過程全被錄下來,掀起軒然大波,但以色列軍方說法,那是拿刀攻擊的嫌犯,所以此案是保衛國家;其後,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對該士兵提出特赦。
「暴力的巴勒斯坦人」,這印記,成為以暴制暴最大的支持者。